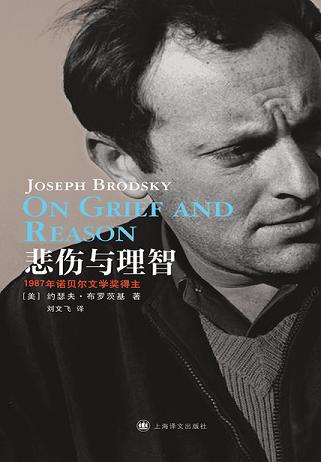
在这部题材丰富、视界浩淼的散文集中,约瑟夫布罗茨基开篇便用深沉内省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在苏俄的早年经历以及随后去往美国的流亡生涯。接着,作者用惊人的博学探讨了诗歌的张弛变幻、历史的本质、流亡诗人的双重困境等一系列颇具广度与深度的话题,思维的触手延揽古今,上及古罗马贤帝马可奥勒留,下至现当代诗人托马斯哈代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美学的炽烈情愫糅合锻造为继《小于一》之后的又一部世所罕见的奇作。
悲伤与理智读后感《悲伤与理智》评语利用碎片化时间,花了一个月才完成这部被誉为布罗茨基文学创作的“天鹅之歌”的散文集。读完之后,对其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有了一个整体印象。在诗歌这片疆土,显然,他是一位出色的统治者,一位出色的守护者。他的散文繁复细腻,让人眼花缭乱,同时也高度规整,充满和谐的韵律感。在《战利品》中,一个俄国孩子,从那些战利品中,洞悉了关于个人主义之优先权的历史证据;《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一个流亡诗人,在众所周知的那座草堆中寻找的一根针——谦卑,这便是流亡的全部含义;《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好的地方》无论一个人的旅行目的何在,是修正他的领土意识,是饱览人类的创造,还是逃避现实,其最终结果,不断需要新的细节以充作其精神夜宵;《表情独特的脸庞》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第二自我》诗人被迫不懈地走向无人涉猎的区域,无论是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他抵达那里。他发现那里的确无人,也许只有词的始初含义或那种始初的、清晰的声音..;《克利俄剪影》作者认为“在从罪孽到救赎这条已得到详尽描述的道路上,自始至终恐怕都没有类似的身影,没有堪比的领悟。基督教一神教存在的任意性,让人类感受走向了历史决定论的陷阱;《体育场演讲》去渴求他人拥有的东西就是在丧失一个人的独特性;在《九十年之后》和《求爱于无生命者》里,用大量篇幅分析了马里亚·里尔克的《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和托马斯·哈代的四首诗。诗人提到的拉丁语中的“诗歌”一词就是阴性的。这极易用于寓喻,而极易用于寓喻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潜意识。似乎在诗里能扑捉到诗人作为“流亡诗人”那漂泊的灵魂深处的潜意识...诗词观:保持语言精准的目的是让一个人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他自己,就是保持其自身的平衡。就整体而言,艺术采取一种自卫的、嘲讽的方式对付苦闷,就是想让艺术成为抗拒苦闷的慰藉,借以逃脱陈词滥调在人类存在中的对应物。美学观:从美学上,认为“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它们非仅仅是“善”与“恶”的范畴。伦理观:在伦理学中之所以不是“一切均可能”,正是由于在美学中也不是“一切均可能”,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哭着拒绝一位陌生人,或是相反要他抱——拒绝他还是要他抱,这婴儿下意识地完成着一个美学选择而非道德选择。政治家的作为也仅限于降低、而不是根除社会之恶。无论一项改进多么重大,从伦理学的观点看它都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永远有人,哪怕是一个人,无法自这项改进获益。世界观:一个人能得到某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制定的规则与禁忌的指引,总胜过仅仅遵守刑法法则。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要尝试不去关注那些试图让你生活不幸的人。就单个人而言,一个个体本身是不构成实施非正义的有价值目标。一对一的比率无法论证付出之合理,起作用的是回声。作为个体,要偷走那个回声,或是让它噤声,无论这个事件多么不幸或多么重大。总体来说,布罗茨基认为,诗歌是人类对语言中的“俗套”和人类生活中的“同义反复”之否定,是个人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悲伤与理智》构成了一曲“关于诗歌的思考”这一主题的复杂变奏曲。他自称,沐浴在诗歌的精神家园里,让他生活得很愉快。它,就像是一扇门、一扇窗,时常是雾蒙蒙的,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看透它;他笔下,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阿德墨托斯王在婚礼时与其父母闹出的乱子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此类场景相形见绌:而出生在色彩单调的俄国,麦克尼斯、奥登和斯彭德的诗使他顿时获得一种家庭般的亲切感,萌生另一种诞生之眷恋。这也解释了为何布罗茨基如此钟爱并在书的开头,引用奥登的这句诗的缘故吧:赞美一切诗歌格律,它们拒绝自动反应,强迫我们三思而行,摆脱自我之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