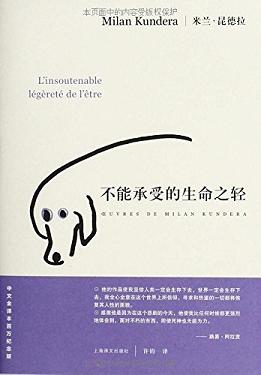
暂无简介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百万纪念版)读后感不要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轻与重的思考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的开篇即说到,1935年埃德蒙·胡塞尔在他去世的前三年,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演讲。在他看来,这超越于地理意义上的欧洲精神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而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然而从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开始,为了实际需要,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成一个简单的、科技与数学探索的对象,将具体的生活世界排除在视线之外了。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陷入到“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中。人被隐去了,被遗忘了。
基于以上的哲学背景,我认为小说中所讨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即“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就像哈姆雷特说的“to be or not to be ”绝非仅仅是“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一个形而上的追问。
小说开头由尼采的“永恒轮回”引出存在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生命一旦永远消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都没有任何意义。”其一因为只出现一次,再残忍的事情也丝毫改变不了世界的面貌。被残害的已经不存在,原谅与不原谅已经毫无意义。由此出现了减罪之情状,这便是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其二这是存在之轻,比空气还轻,飘起来,是半真的存在,其运动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其三这是人的本真状态,在人的局限性范围内无能为力,没有借助任何外在工具来代偿人本身存在的缺陷。其四托马斯这一人物便是由“偶然一次不算数”这一句子脱胎而来,他本身就是自由着,如果上帝没有把特蕾莎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着河流漂来的话,就没有他的“非如此不可”。他像上帝一样冷漠自由的窥伺着每一个人的不同,将世界缩减成一个简单的探索对象,将具体的生活排除在视线之外。这是存在不能承受的轻!
与此对立的便是“永恒轮回”,“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得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是残酷的一面,即特蕾莎被肉体的囚笼压的闯不过气来。“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这是存在的沉重美的一面。正是有这沉重的负担,生命才如此真实,托马斯才在他仅有一次的生命中有如此多的“非如此不可”。这样的沉重丰富了存在,丰富了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凭着第一次阅读残存的记忆,再次翻起这本书时,我其实只是单纯的想重温一遍托马斯与特蕾莎的复杂爱情。然而再次翻完后,我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重大的人生秘密似的,即使这样的感受早就成了很多名家老年回忆录中或者是经典阅读的课堂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自己所体会的东西和别人传输给你的知识点始终是不一样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阅读同一本书所关注的点所体会的东西会有很大的差异。就像一个人一生兜兜转转了一圈,你四岁时与妹妹所打的架是一个事实,可是你八十岁时回忆起这件事的感受和你四十岁的回忆,以及你四岁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事物每次激发出不同的含义,但这含义中回响着之前曾有的所有含义”。即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这含义层累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存在的厚重。
那时年纪尚小,整日沉浸在杂志月刊的青春文学中,满脑子是华丽辞藻堆积起来的风花雪月,所谓的伤感所谓的深刻皆是一群尚未经历人间疾苦的小姑娘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因此第一次阅读这本小说对我还是一个蛮大的冲击,托马斯与特蕾莎的另类爱情是其一,人物的多面向冲破了我以往对人物单一向认知是其二,作者对“媚俗”以及“灵与肉”等问题的经典阐述是其三。在这基础上这些经典名言满足了我伪文青高逼格的文艺癖好是其四。由于以上四点对我的冲击,我开始困惑于托马斯的复杂人性,我好奇于人的存在,于是便不自觉的从杂志月刊中青春文学的阅读向外扩展,从这《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年少懵懂的困惑出发,离开原本封闭的知识家园向外远游,开始阅读文学经典,阅读历史,阅读哲学等等,以求明我之于人性的困惑以及我之于存在的好奇。
但是在这条河里游着游着,我发现我没有了目标,每天都在纠结自己游泳的姿势是否合格是否正确,抬起头来,没有了彼岸,只有涛涛洪水中茫然的挣扎。最初我是带着问题进来的,现在连问题也弄不清了。但又和最初的懵懂是不一样的。最初的懵懂,脑子里是空白的,而此时装下了太多自以为是的东西,往往会迷失掉最本质的东西,陷入了“对存在的遗忘”的状态中。这时要像托马斯一样追问一句是不是“非如此不可”呢?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不要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不追往事,仅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发,我想我该从中找回我最初对人生的疑惑,不要掉入陷阱里。欧洲是否能在这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人类是否能在新一轮科技危机之后继续存在,我想无关乎轻与重的残酷还是美丽,重要的是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是不是“非如此不可”。